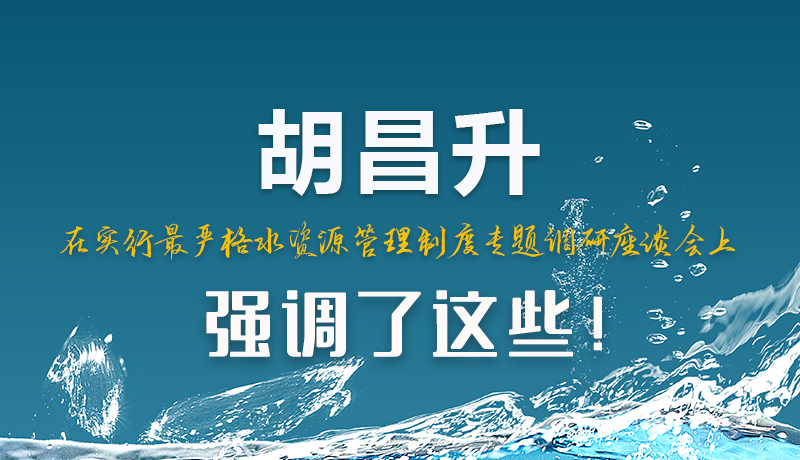張勇敢
曾祖父去世后的第五年,我寫了一首詩紀念他。這首詩簡要地描述了他的一生,我記得他是釀客家米酒的老師傅,記得他膝下無兒無女,收養了我的爺爺,記得他在病床上骨瘦如柴,記得那是6月的最后一天……
寫詩,是我想到的最好的紀念方式。
用詩歌寫作來記錄生活、表達情感已成為我最重要的習慣。打開世界大門的鑰匙有很多把,我的這把就是詩。
初中一年級,我在語文課本上讀到的第一首現代詩,是王家新的《在山的那邊》。我永遠忘不了那種感覺,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“受到了一點小小的震撼”,原來還有這樣的文學體裁,原來情感還能這樣表達。短短幾句分行,就把想說的和未說的都寫了出來。從那時開始,我慢慢嘗試寫詩。
正值青春懵懂的年紀,最先被我寫進詩里的是對愛情的憧憬、對未來的幻想。而當我遠離家鄉,去重慶上大學,各種和故鄉有關的意象才真正出現在我的詩歌中。
我的家鄉福建寧化,被稱為“客家祖地”。我們村有個頗為文藝的名字:半溪村。小時候,我們總是上山砍柴火、摘野果,拿著簸箕去小水溝里抓魚,在雜草叢中過家家,或者在秋天等水稻割完后,跑到田里掀開谷堆抓田鼠。這些經歷都被我寫成了詩。
除了田野,在詩中出現最多的就是我的父親母親。我正式發表的第一首詩就是《穿上母親的鞋快離開吧》。我的父母親都是農民工,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在福建沿海一帶打工,只有暑假時,我才能去見他們。從上大學到工作后,我回家的次數變少了,對家人的思念都變成了文字,我寫下《與母親讀詩》《五月了,媽媽》《父親》《中年綠植》等詩歌。大學畢業時,我印了一本詩集作為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。在自序中,我寫道:“生而為木,獨木成林。”在寫下這些和故鄉、和親人有關的詩時,我感到有一種力量油然而生,支撐著一顆離開土地的小種子,慢慢學會找到屬于自己的土壤,并生根發芽。
“詩歌為我建造的世界早已遠大于現實的世界,通過每一個詩人,每一首詩,我親臨了無數個現場。”這也是在自序中寫下的文字,現在看來依舊如此。
當下,人工智能爆火,只需要輸入明確的指令,人工智能就可以洋洋灑灑寫出幾百字的詩,寫一首詩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。但是真正源自內心的對土地的熱愛、對生活的熱愛,是人工智能永遠無法體會和取代的。
我出生于1994年,我們這一代寫詩的年輕人被貼上了一個標簽——90后詩人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這個簡單直接的稱呼,和我們寫作的風格無關,和我們表達的想法也無關,卻從一開始就和時代緊密關聯。上世紀90年代是變革的時代,在這個時代中長大的90后詩人,被這個時代命名,同時也在寫作中記錄、感激這個時代。全球化浪潮、城市化進程、數字時代……這些詞語陪伴著90后詩人長大。但我們同時也是矛盾的,一方面親近土地,帶著持續消解、不斷重構的童年記憶,一方面離開土地,逐漸呈現出明顯的“異鄉人”身份和視角。詩歌,在此時提供了情緒的出口、情感的依托。在詩歌中,我們努力尋找一種平衡,在裂縫之上搭建橋梁。
很喜歡一部電影——《尋夢環游記》,“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記得你”,這句臺詞戳中人心。我總是把詩歌當作日記來寫,就是希望記住什么,是擦肩而過的某人,是一場令人驚嘆的黃昏,更是我熟悉的土地,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。也許我能寫下、能記住的不多,但我仍然堅持寫下去,每每讀起那些詩,也總有一種“常回家看看”的感覺。對于離開故鄉生活的年輕人來說,又何嘗不是一種“返鄉”呢。
- 2025-05-09共繪隴原文旅美食新畫卷——“看視頻 品美食 去旅游”甘肅省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創作宣傳推進會在蘭舉行
- 2025-05-08蘭州職業技術學院舉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題宣講
- 2025-05-08甘肅省首家“麒麟工坊”實訓基地落地蘭州職業技術學院
- 2025-05-08蘭州城關區青少年運動會暨市十運會選拔賽燃情啟幕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
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
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
今日頭條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