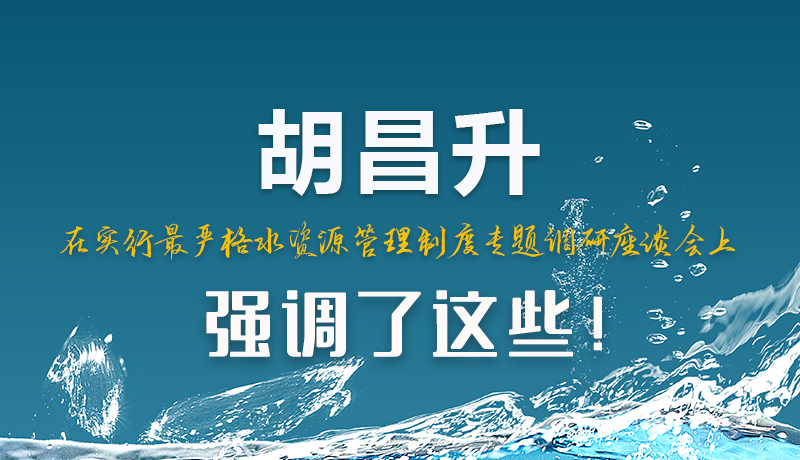王 勇
我的作品中有五部比較特別——“一個人”,表現青蒿素發現者屠呦呦的歌劇《呦呦鹿鳴》;“一座碑”,以石匠為主人公的河北梆子《人民英雄紀念碑》;“一艘船”,致敬中共一大“開天辟地大事變”的歌劇《紅船》;“一本日記”,講述“人民至上,生命至上”的抗疫題材歌劇《天使日記》;“一封信”,寫愛祖國、愛家鄉、愛親人的華工華僑的歌劇《僑批》。
這五部作品都是“大題材”,但無論題材多么重大,“言情化”的創作理念始終不曾忘卻,即“寫人”,寫具體、生動的人,寫能引發同頻共振的情感。
比如,面對“人民英雄紀念碑”這樣宏大的題材,既可以領袖為主角,也可以碑體設計者梁思成和參與設計的林徽因為線索,還可將吳作人、劉開渠等畫家、雕塑家敷演成劇。然而,曲陽石匠們的故事始終吸引著我。石匠是人民的一分子,是最普通、最樸素的一分子,普通的石匠雕塑人民英雄才更有意義。于是,我寫的河北梆子《人民英雄紀念碑》選擇從“刻小碑”升華到“刻大碑”的無盡感嘆,凝練成“人民創造歷史,歷史造就人民”的宏大主題。
回首創作之路,真善美,始終是主線。舞臺就是藝術家的天地。我們一面叩問往昔,一面塑造未來。正如一個巨大的鐘擺,當它側首回顧的幅度越大,遙寄未來的距離才能越遠。
12歲那年,我在家鄉藝術學校學習采茶戲,那是一種流行于江西西部的“三小戲”。學戲并非我的主動選擇,但看了京劇電影《白蛇傳》,我被深深吸引。《白蛇傳》劇本是田漢寫的,我當時一連看了三遍,越看越喜歡。傳奇的故事、幽幻的意境,那些“看斷橋、橋未斷卻寸斷了柔腸”“猛回頭避雨處風景依然”的唱詞,文辭背后溫潤的筆觸、細膩的情愫,還有劇作中蘊含的真善美,直擊我的心弦。14歲,我寫了平生第一個兒童劇劇本《啄木鳥》。
40多年的編劇生涯,讓我逐漸認識到:真正優秀的作品是詩性的、言情的。戲劇理論家張庚有“劇詩”一說,闡釋中國戲曲藝術的本質特征在于“詩化”,即劇作也是一種詩。這一理論給我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記。冥冥中,我覺得兒時愛背詩的自己,最后走上編劇之路,或許就是一種“注定”。而紅學家卜鍵老師講述的戲曲類型化、程式化、言情化,對我的創作幫助頗大。詩性表達讓藝術與生活保持距離,且高于生活;言情化創作就是寫人,寫人的情感。
無論創作經歷,抑或工作經歷,所有的人生歷練都是彌足珍貴的積累。我的創作涉獵戲曲、話劇、兒童劇、歌劇、音樂劇、舞劇等不同藝術門類。戲曲則包括京劇、黃梅戲、贛劇、越劇、評劇等十幾個劇種。我還學過表演、當了編劇、搞過研究、干了管理。其間,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經歷對我的成長影響深遠,在那所幾乎涵蓋了所有藝術門類的學府里,我像海綿一樣吮吸著豐厚的養分。不同藝術門類的特點,融匯到我的創作中,逐漸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。
今年,我給自己定下了新的創作任務:一部話劇《水木清華》,講述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的故事;另一部是歌劇《南遷》,講述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;還有一部地方戲,通過一株茶樹、一片茶葉,講述茶的故事、茶人的故事。
梨園行里,寫劇本的被叫作“打本子的”。我或許干不了別的,只能“打本子”。人這一生很短暫,在有限的生命里,能夠做好一件事,也就是“擇一事,終一生”,就已“善莫大焉”了。
(作者為一級編劇、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、國家京劇院院長)
- 2025-05-15戶外勞動者有了“工會驛站”
- 2025-05-15八方速遞
- 2025-05-15超過5300米 我國頁巖氣井垂深紀錄刷新
- 2025-05-15“土壤抽鹽機” 改良鹽堿地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
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
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
今日頭條號